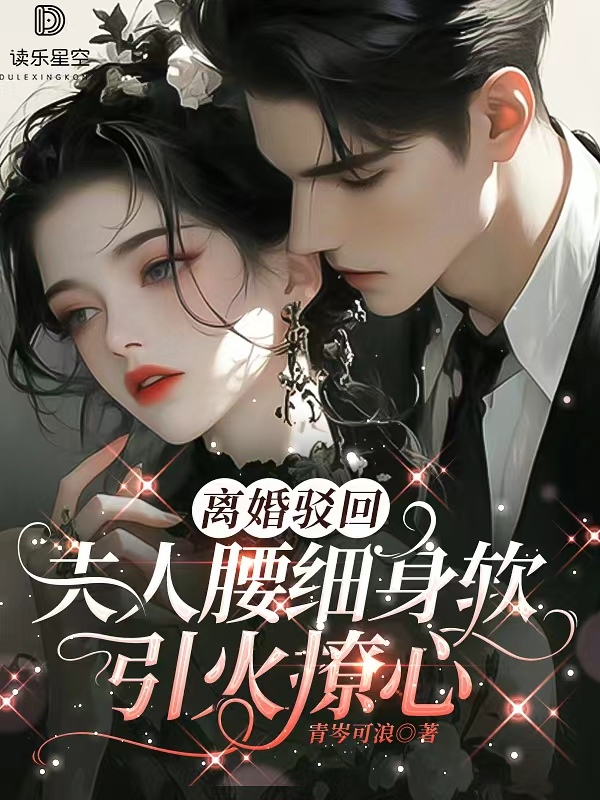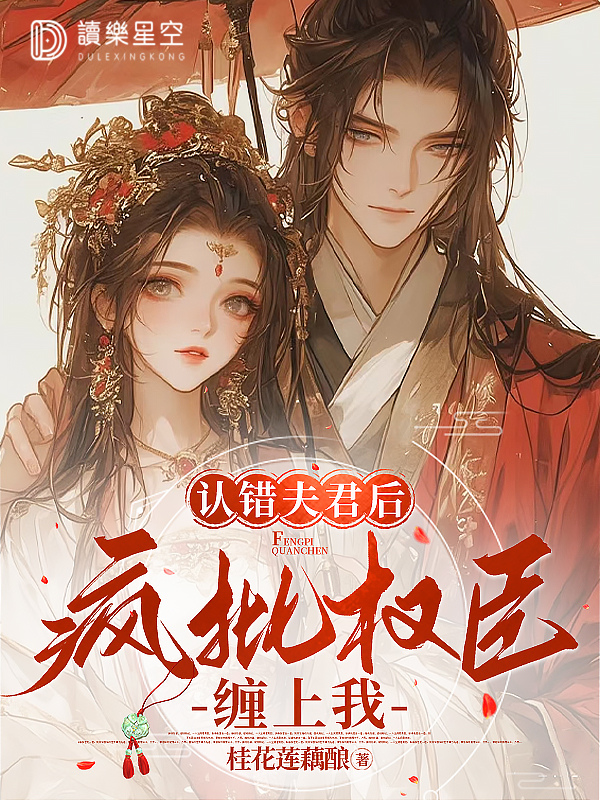十五
照理,对于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,不必再作这种衡量。但是,这三个世纪,对中华民族实在是至关重要。十六、十七、十八世纪,正是我在《中国文脉》一书中论定的数千年中国文化的衰落期,也是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的时期。
且不说经济和政治,只在文化上,就有一系列令人心动,甚至令人心酸的比较。例如——
昆曲开始发展的时候,正逢西方地理大发现已经完成,文艺复兴正在进行。就在汤显祖十四岁、沈璟十一岁那一年,英国的莎士比亚诞生。十年前,魏良辅的女儿嫁给了张野塘。
有学者考证,一五九一年汤显祖在广东见过西方传教士利玛窦,这是徐朔方先生的观点。我比较赞成龚重谟先生的看法,汤显祖见到的西方人也许不是利玛窦,可能是罗如望和苏如汉。但不管怎么说,我们的昆曲作家与西方近代文化已经离得很近。显然,在任何一个意义上,他们都“失之交臂”了。昆曲在汤显祖之后,没有太多进步,却依然还是占据中国文化的要津,那么久远。而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,莎士比亚之后的欧洲文化,却不是这样。
李渔与莫里哀,也只相差十一岁。
我又联想到十八世纪后期的一个年份,一七九二年。那一年,汇辑流行昆曲和时剧的《纳书楹曲谱》由叶堂完成,昆曲也算有了一个归结点。但是,我们如果看看远处,那么,正是这一年,法国《马赛曲》问世,莫扎特上演了《魔笛》并去世,海顿成为交响曲之父。而仅仅几年之后,贝多芬将贡献他的《英雄》和《田园》。
相比之下,我们如果再回想一下吴梅所揭露的多数昆曲的老套,就知道当时不同文化之间的方向性差异了。
这种方向性差异,后来带来了什么结果,我就不必再说了。
我并不是要在比较中判定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绝对优劣,而只是想说明,中华文化即便在明清两代的衰落时期,本来也有可能走得更为积极和健康一点。
文化,除了已经走过的轨迹外,总有其他多种可能。甚至,有无限可能。
不错,存在是一种合理。但那只是“一种”,而不是唯一。而且,各种不同的“合理”分为不同的等级。文化哲学的使命,是设想和寻找更高等级的合理,并让这种合理变为可能。
因此,我们面对一个伟大民族在文化衰落期的心理执迷和颤动,都应反思,都可议论。
昆曲,是我们进行这种反思和议论的重要题材。
癸巳年元月改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