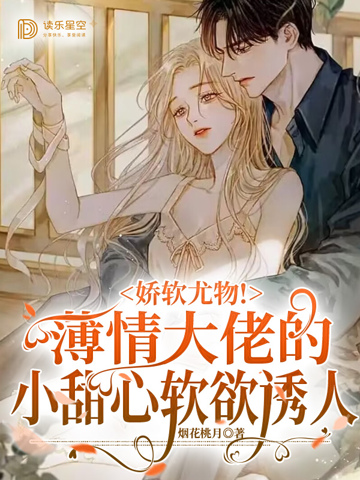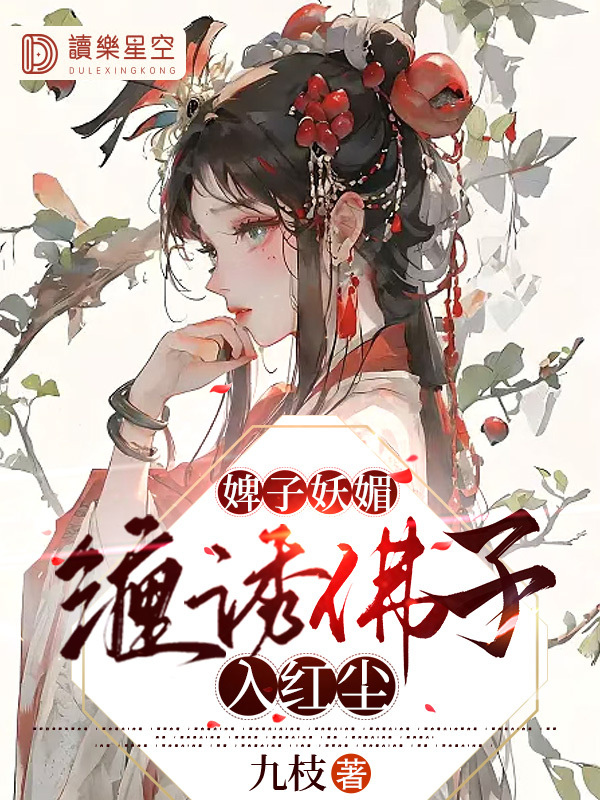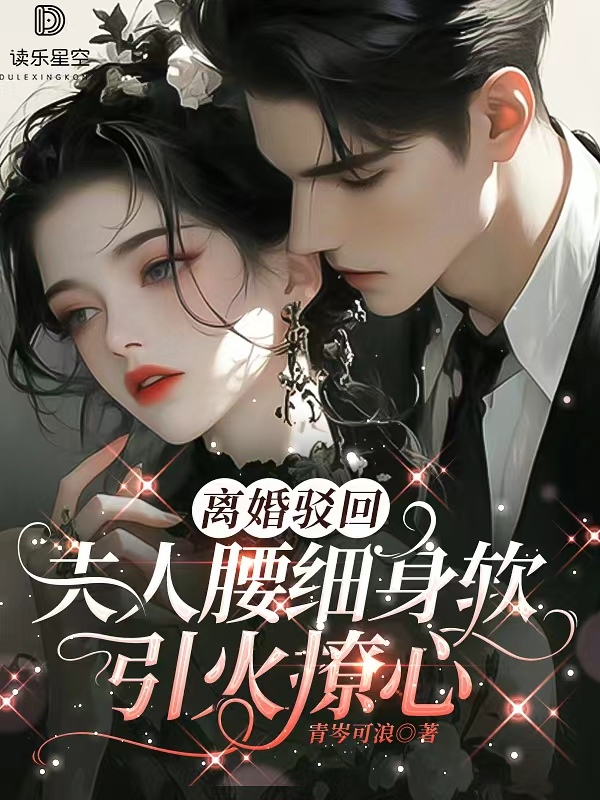1.文学的魏晋(1)
公元584年,隋治书侍御史李谔,认为“当时属文,体尚轻薄”,于是上书隋文帝杨坚,要求领导采取一些措施。从此人职务上的“治书”二字看,显然是政府里主管文化方面的官员了。
大凡帝王跟前的这类文人,特别容易患有意识形态恐惧症,稍有风吹草动,立刻会敏感地东闻西嗅,寻找动向。他说:
“魏之三祖,崇尚文词,忽君人之大道,好雕虫之小艺,下之从上,遂成风俗。江左齐梁,其弊弥甚。竞一韵之奇,争一字之巧,连篇累牍,不出月雾之形,积案盈箱,唯是风云之状。世俗以此相高,朝廷据此擢士。禄利之路既开,爱尚之愈笃……以傲诞清虚,以缘为勋绩,指儒素为古拙,用词赋为君子,故文笔日繁,其政日乱……”
李谔,也真是好一个了得,一下子寻本追源,把账算到了二百多年前的“魏之三祖”的魏晋文学上。九泉下的曹操、曹丕、曹睿,被他这样一上纲,实在是一头雾水,很莫名其妙,儿孙不争气,与老祖宗何干?
从历史上看,“左”一点也是要比右一点便宜,李谔因此得名,在《隋书》里,作为正人君子的形象,有传存焉。其实,此公心地不怎么样良善,看列传里他的一些作为,估计他是一位面色永远铁青,终日不苟笑,以整顿世风为己任的清教徒。
这类“左”大爷哪个朝代都会出现的,而且总在上风头站着。
他曾经捣鼓杨坚布了一个五品以上官员死后,其妻妾不得改醮的命令,居然明文立法,强迫妇女守寡,可见其是多么令人憎恶了。因此,这个道德狂,没事找事,上书隋文帝整风,规范士子,是做文化警察的这类人再正常不过的举动。
要不然,这世界太太平了,他不就失业了嘛!
杨坚本人,生性忌刻,不喜词华,一览李先生的奏章,认为正合孤意,随即下令全国“公私文翰,并宜实录”。不许繁文缛节,玩弄词藻。凑巧有个倒霉鬼碰上了枪口,“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,付所司治罪”。这位刺史本想露一手,结果却因自己的骈体文、四六句做得太出色,而交付检察机关定罪。玩文学,玩不好,而玩出漏子来,他不是第一个,也不是最后一个。有什么办法呢?司马先生只好为他的漂亮文章蹲班房了。
李谔之所以如此痛心疾地开展文化批判,也并非绝对的无的放矢。当其时也,文学之矫造作,华而不实,玄虚无物,夸浮伪饰,已成文人笔下的痼疾,也实在令人摇头。
与他同朝做官的学者颜之推,此人先在南梁为仕,后在北齐做官,最终在隋朝任太子学士,可谓见多识广,他在他的著作《家训》中,讲到南北朝时的文风时,也是嗟叹不已,很不赞成的。
他举例说:“近在并州,有一士族,好为可笑诗赋,誂撇邢、魏诸公,众共嘲弄,虚相赞说,便击牛酾酒,招延声誉。其妻,明鉴妇人也,泣而谏之。此人叹曰:’才华不为妇人所容,何况行路!‘至死不觉。”
“有一士族,读书不过二三百卷,天才钝拙,而家世殷厚,雅自矜持,多以酒犊珍玩,交诸名士,甘为饵者,递共吹嘘。”
因此,颜之推说:“音辞鄙陋,风操蚩拙,相与专固,无所堪能。问一辄数百,责其所归,或无要会。邺下谚云:’博士买驴,书券三纸,未有驴字。‘使汝以此为师,令人气塞。”
买一条驴的字契,写满了三大张纸,还没有提到一个驴字,若放在今日文坛,各式新潮评论家不赐以这位博士超现实主义大师的桂冠才怪。而从举例中所说的“虚相赞说”、“招延声誉”、“交诸名士”、“递共吹嘘”来看,与时下常见的有偿评论,受雇吹捧,收费叫好,红包文章等等手法,如出一辙。事隔千年,似乎历史被定格了一样,也真令人扼腕。看来,文学虽然进步,但作家们求名自售时的不择手段与无耻无赖,甚至愈到后来愈下作。
但这一切的堕落,与魏之三祖,和以他们为代表的魏晋文学无关,他们并不应负南北朝文风颓靡之责,这是李谔错误的判断。任何事物,包括文学的潮流,哪怕具有极好的开始,也会因缘时会,而产生出完全背离初意的后果。新时期文学的性描写泛滥,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其规律似乎是这样的: